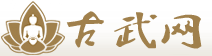背负仇恨而游荡江湖,无论这仇恨惨重到瞬息之间家门遭毁、父母皆亡,如《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还是轻盈得近乎喜剧,最终居然是一场误会,如《天涯·明月·刀》里的傅红雪,让仇恨成为生命向上攀升的内在动力,甚至是一种维系精神挣扎的终极信仰,这是武侠叙事的常态,也是世界的常态,江湖不过是人世的一个翻版。丧失了仇恨冲荡的世界,注定只是遥迢而不可企及的田园牧歌,是江湖之外的虚幻江湖。有仇恨才有江湖,仇恨沉淀在个体的人格之中,构成一种最本原的价值,这决定着他为什么活着,以及怎样活着。对傅红雪而言,他出生的时刻,触目之处,鲜血染红了天降的大雪,以“红雪”命名,似乎暗示着他的终生都将无法挣脱仇恨的束缚,他的生命就是一次次的拔刀、击刺,可一旦当他知晓,他的仇恨只是一次命运的错位,一个偶然的玩笑,他便没有理由不虚无下去,仇恨的失落解构着生命的意义。再如《天龙八部》里的萧远山,当无名老僧将他的仇人慕容博一掌击得气绝,他顿时感觉心气虚弱,“犹如身在云端,飘飘荡荡,在这世间更无立足之地”,这是因仇恨消逝而导致价值迷失的一例,他的终极归宿是皈依佛门。当然,还有因仇恨而疯狂的林平之。
林平之的身世虽然可以说上崎岖婉转,但在正统武侠的传奇叙事中,却并非足够惊艳。他首先是“夺宝游戏”(争斗林家祖传的《辟邪剑谱》)中的受害者,接着便成为“复仇游戏”(报杀父杀母之仇)中的行动者,同时还是“情爱游戏”(与师姐岳灵珊)中的背叛者——正是这三大游戏及其之间的缭乱缠绕,绘制着武侠小说的诡异容貌。林平之担负的三个角色引导着叙事走向纵深,可在《笑傲江湖》之中,他只是一条颤动的暗线,一直处于隐晦而被冷落的地位。对小说的读者而言,他可能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他被当成第一主角的出场及逃亡的假象,或许还有他与岳灵珊畸变惨烈的恋情。除此以外,确实难以在他身上找出特异别致的一面。
但这个人还是深深吸引着我。这种吸引,有着同病相怜的气味。在健康的自由主义者令狐冲的映照之下,林家少年是如此病态,如此苍白,这时常让我想起叶开与傅红雪的反讽对比:应然的复仇者明朗欢快,错误的替身却阴郁冷漠,即使他们都晓得了这是一场误会,既定的状况也无法改动。仇恨之于林平之,如同之于傅红雪,决然占据着生命领地的全部。他上华山以后,也是如傅红雪一样,在仇恨的驱使下疯魔般地苦练剑术。与岳灵珊的情事仿若复仇的无意点缀,婚姻成了铺垫的阶梯,为了复仇他不惜自宫,让婚姻有名无实。这在另一面正显示了他复仇之心的勇猛和决断,他的精神出路已为仇恨的火光所彻底宰制。我一直以为,金庸小说中最接近浪子傅红雪的一个,就是林平之,尽管他们的收尾不同,但精神姿态却是一致的。
为了复仇,一切都可以舍弃,林平之奔赴在复仇征途上的决绝,甚至癫狂,是金庸抒写人性的一个极点,这个极点还可以表现在左冷禅与岳不群对待权力,曲洋与刘正风对待艺术上。仇恨滋生的极端心态蒙蔽了林平之的眼睛,使他看不清远方以远的道路,因而他的诸多作为显得相当急功近利;同时也深重限制着他年轻的心灵,他的心理永久滞留在父母被杀的那个血腥夜晚,尽管岁月飞逝,仇恨的阴影却阻止他走向成年。称呼比他幼小的岳灵珊为“师姐”,一面是进身师门的策略,而在另一面,这也不自觉地限定了林平之的孩子气的沉积。一个孩子的疯狂,比起一个成人的疯狂,即便是同等举动,也会呈现得更为粗暴和冷酷。所以我们不必对后半部《笑傲》中林平之的狂暴形象表示诧异。孩子式的固执,还有自宫后的偏激和身份迷乱,只可能加重仇恨之火对他的烧灼。同样,他会以相等或者更为过头的力度报复他的仇敌,等到恩怨了结,他的报复对象便转变为他身边的整个世界,漆黑的华山山洞里,双目皆盲的林平之叫嚷着要杀与他并无仇怨的令狐冲,表面上看似一个疯子的行为,实际上正符合仇恨心理极端化的处事逻辑。
林平之终于成功复仇,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眼睛被驼子木高峰的毒水喷中,凄然失明。这一结局让我想起希腊时代的俄底甫斯,他最终也落得目盲的命运,当然,他是自己挖去了眼睛,以惩罚所犯下的罪行。后世的思想家们将俄底甫斯的“弑父”诠释为成年的礼仪:推倒父亲在精神上的权威,宣告着个体生命成年的开端。而在中国传统里,成年仪式必须由“父亲”这一权威主持;转化到武侠小说里,可以勉强命名为“寻父”情结,如与林平之遭遇类似的杨过,如果没有郭靖的现身,没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淳淳教诲,恐怕神雕大侠很难尽早脱离复仇的不归路,曾被当作他的杀父仇人的郭靖正是他的精神父亲,当他认信于郭靖的权威,积压在心头的仇恨便被祛除,偏执莽撞的少年也便迈入成年的稳重大门。所以,对于复仇者而言,至为关键的,不是如何复仇,而是学会如何看待仇恨,后一个问题得以体悟之时,正是这个人实现成年之日。
林平之与俄底甫斯都失去了眼睛,但一个疯狂,一个清醒;一个始终徘徊于未成年的边界,一个越过成年的路标,开始洞悉命运的玄机;一个被锁进西湖的地牢,在黑暗中继续着对世界的仇恨,一个通过对自我的放逐,与命运的神灵拉开了距离,这使得他有机会去批判那条早已指定的路途,这种人,至少可以被奉为智者。智者是热爱这个世界的,而一个内心充盈着无边仇恨的人,对世界的态度,却是绝望死寂。林平之不可能成为智者,他的自宫,割去的不仅仅是肉身的阳具,更是与这个世界的无尽牵挂:爱、信仰、希望。或许可以说,于林平之个人,“自宫”正是他的成年礼,那一刻发生的身份与精神的转机,可以视为他与世界签订了新的盟约,自此他的怨恨指向不再是那些具体的人,而是整个冰冷的人间。这是一种刻毒的成年,那个温顺文雅白衣飘飘的富家少年的影子,被一个遗失了性别的迷惘者无情遮蔽。他弑去的是世俗的规则。这种惊世骇俗的成年,只存在于我的狂想之中。
自宫以前的林平之一直生活在无望与耻辱里;之后的他又将在惘然和混乱的价值河流中飘荡。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他都是一个极端悲剧的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密切牵系着我们的灵魂。这是所有未成年人的特性,被某种神秘力量压制后的敏感忧郁、自信以至狂妄,神经质或者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