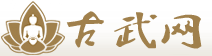想到浪子,总会想到令狐冲。浪子,是个充满诱惑和潇洒的称谓。或许是烟花柳巷中寻寻觅觅的风流倜傥,或许是西风瘦马对酒当歌的。金庸笔下没有比令狐冲更像浪子的人物了,他放荡不羁、散漫成性。他在行为上可能绝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他在精神上却是规矩的再也不能规矩的清教徒。
太多人包括金庸自己在内,总会视令狐冲为“隐士”。那是观者名利太过熏心的结果,只看到门派舞台上的角逐。不追求名利,向往自由而无拘束,便是隐士;说罢庄子曾经曰,便搬上讲台娓娓道来。而淡泊名利于令狐冲,那不过是天性的自然流露,“隐士”或可形容他的职业,却并不能道明白,他拥有怎样的内心世界。
金庸笔下的主角,仆一出场便带着满身酒气的惟有令狐冲。衡阳城内华山派诸位弟子,提起大师兄,一个个眉飞色舞的样子,多让人想起小学生眼中的高年级学生,看起来威风八面——却毕竟还是个孩子。当然孩子也会长大,《七剑》中风火连城说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了魔鬼,那又是另一说了。
此时的身为华山派大弟子的他,有师父的悉心调教,有师母的慈颜照料;有活泼可爱的小师妹青睐,更得一众华山弟子的前呼后拥;此时的他,至情至性如白玉一般,纵然放荡不羁,纵然嗜酒如命,纵然不拘一格。却不过是一个没有经历人情冷暖孩子。此时的他,心无旁骛,何曾识得愁滋味。他有浪子的潜质,却不一定会有浪子的人生!
如果不是《辟邪剑谱》掀开一番腥风血雨。或许娶得娇妻,承岳不群衣钵,做一个小小华山派的掌门;便是他潜意识中终极人生目标。偏偏造化弄人,隐隐的一根命运之线,将福威镖局、青城派、五岳剑派、黑木崖牵在了一起。岳灵姗、林平之、令狐冲、任盈盈,这几人的命运,如同这根线上的几只蚂蚱!
浪子,永远都带着漂泊的味道,漂泊而居无定所。对于男人而言,最辛苦的漂泊不是躯壳的流浪,而是灵魂的无所皈依。那皈依的所在,便是心灵向往的地方;或是慈母的身旁;或是梦中恋人的怀抱。
令狐冲曾经自我设定了极其美好的精神家园。只是不经意间在岳灵珊福建山歌的歌声中变得支离破碎。岳不群夫妇带领华山派走下华山之时,令狐冲颓废潦倒,固然因内伤而起;更重的怕是终日看到林岳二人之卿卿我我;还有岳不群一副道学先生面孔的终日猜忌。
此时的令狐冲是精神的流浪者;因为没有真正可以慰籍的家园。或者在浮沉,或者在麻木;就那样无所事事地、颓废地飘着。是一种欲求而不可得的孤单,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浪子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有颗纯洁晶莹的心灵。洛阳城内,那一声“婆婆”不经意间抒解了任盈盈的芳心。那一次号啕大哭,似是令狐冲心中怨结的释放,也是另一处心灵的海市蜃楼在慢慢拉开帷幕。
在令狐冲人生的低谷,任盈盈硬生生地给拉出了逆势上扬的阳线。绿竹翁轻轻一挥手,将金刀王家的两个小孙子扔进水中时,不经意间奠定了令狐冲日后的基调。任盈盈是一个爱的守侯者,默默地守侯着一份自己的期望。
令狐冲于岳灵珊可能是玩伴、可能是保护者、照顾者,而令狐冲于任盈盈,却是平等的爱的身份。任盈盈理解他的心思,知晓他的情之所牵,愿意为他做让他开心的事情,即便是为了别的女子。她等这个男人等了许久,直到青纱帐的大车里,心里默念道:“原来你还是在乎我比在乎她更多些。”才知道自己终于等到了。
任盈盈为令狐冲重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她不是一个小气的女子,冷静而聪慧,皇天不负,这个傻傻的男人懵懂无知地跌跌撞撞,终于找到了这里。相对天真浪漫的女孩,男人更需要一个懂得爱他的女人,这才是完美的归宿。
武侠的动人之处,便是将人带入那虚无缥缈的江湖。让人感受到生活浪漫主义的升华,不知不觉中,主角便是自己,自己便是主角。心灵跟随着人物的脉搏在栩栩如生地颤动,带着活生生的喜怒哀乐。
佛门谓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爱怨憎、恨别离、求不得!浪子不在乎生老病死,不在乎爱怨憎、恨别离;却在乎求不得。令狐冲不缺乏拔剑与天下战的勇气,但是倘若没有任盈盈的执著和这最后的归宿,令狐冲才是真的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