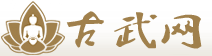五禽戏体现了人和动物都有生命。但是人除了有与动物相同的生物生命之外还有动物所没有的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美是人的生命需要的精神实体。当人的生命需要以精神的方式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产生了美感。针对人的三重生命而言,美来自对人的三重生命的“不同”满足。由于人的生命拥有不同的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值,因此,这里的“不同”既指对三重生命各层面的满足,又指对三重生命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满足。又因为人的三重生命之间的比重虽然不是完全相等,但是三者之间又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某重生命的畸形庞大或者某重生命的过于葵缩都会影响整个生命的发展甚至存在,所以这里的“满足”,其最低标准就是使某层生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最高标准则是调整三重生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使三重生命最终达到和谐,从而更有利于人的生命这个整体的发展。从人的生命这个立体存在出发看五禽戏问题,可以发现:首先,它可以满足人的不同生命层面的需要。对于人的生物生命而言,它能够从调气的形式满足人们的某些错求。三重生命的基础是生物生命。人这种离级生物作为自然物的一种,其内心潜藏着深沉的和大地融为一体的心理冲动,一种回归自然的本能,这也就是勒弗劳克所提出的产该亚定则”气自然是五禽戏最主要的资源,因而人能够在练习五禽戏中通过与大自然的物我交融,仿佛回到母亲怀抱般的“回归体验”,产生极大的安全感、舒适感、审美感。身体的健康是生物生命旺盛的标志,五禽戏能够满足人们生物生命的需要,更能有利于生物生命的发展。
对于人的精神生命而盲,五禽戏有两方面的积极功能。其一,心理学认为,当特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外在环境刺激物通过人的感官进人大脑,就会被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比较辨析器推导,产生自觉认知式的愉悦。这种被称为“无意识推理’的心理运动过程,不同于对自然的本能性的“回归体验”,因为它是在人的后天通过长时间的生活实践所积累产生的。但是这个过程极其神速,以至于连愈识领域都难于觉察。对五禽戏而育,具有审美价值的外在环境刺激物是五禽的“象”。因此,人们在长期的练习过程中,受到“立象以尽意”的美学感染时,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偷悦感受。其二,练习者在面对具有特色的景观时,受其形、声、色等特殊条件的影响,往往产生无尽的想象,这些丰富绮丽的想象能使练习者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超越感,超越现实和物质的限制,构筑起无限的精神时空。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无法达到的,都可以在精神的世界里得以实现,所以,五禽戏特别讲究练习环境的优美,毕竟,它能使练习者产生新奇感,摆脱在日常生活环境中造成的审美成劳,从而在好的环境和氛围的刺激下产生理的感悟、情的激动和艺术灵感的沟通,在山川风物所蕴含的特殊的文化氛围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的社会生命而言,五禽戏有两个方面的满足。首先,它是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正式被国家确认为我国第97项体育运动来开发研究与推广。作为一种大众性活动,在练习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相对平等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哲时谈化了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因职位的高低、权利的大小、财富的多少等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从而也减轻了人们心中因这些因素造成的压力。同时,在练习中感受到的与日常杜会生活习惯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使平时不得不严格按照社会运行规则安排自己的生活,长期被杜会意愿压抑自己个性的人们得到放松,得到休憩。其次,人们在练习中,通过对五禽的感悟,真切体会到自然的美丽伟大,从而产生保护自然保护动物,保护人类家园的强烈贵任感。
从人的生命的三个维度来看,五禽戏能够分别满足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需要。因此,从三重生命这个系统来看,通过练习五禽戏(包括各种文化理论的学习),可以使人某个原本薄弱的生命层面得以强化充实,以调节三重生命之间有时出现的不正常的极端不平衡状态。通过这种调节,三重生命达到和谐发展,而人也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和谐”这个概念,并不是对于三重集命之间关系的静态描述.而是必须与“发展”这个动态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只有最大可能地保证人的整个生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和谐。因此,要达到这种“和谐”,就必须从生命的三个维度立体地、全面地、系统地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也必须在现阶段生命要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尽可能从未来可持续的角度制定练习计划。三重生命的不平衡和三重生命的和谐发展并不矛盾,和谐发展是不平衡的基础,也是不平衡的目的。个人的发展,来自于整体索质的提高,也就来自于三重生命的整体性提高,只有在三重生命都得以相应满足的基础上,才能为某一重生命的突出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否则,根基不稳,必然导致畸形和偏执。
不重视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一味强调生物生命的人,最终只能获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评价;忽略生物生命和社会生命,过度沉迷于精神世界的人,很可能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而漠视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过分张扬社会生命的人,则更有可能在社会中失去自我,成为社会机器上没有生命力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