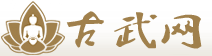全真教本来是由王重阳创立的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道教新派别。王重阳、名哲,字知明;又名德威,字世雄;号重阳或害风;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卒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黄河流域逐渐落入金人之手这样一个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他青年时代“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天春间(1138—1140年)……捐文场、应武举”,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十分孱弱,舍弃广大北方领土和人民不顾,苟且偏安,使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加之,他本人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不到北方人民群众的伟大反抗力量,找不到反抗异族暴掠的正确道路,在金人的残暴统治和伪齐政权的高压之下,于四十八岁上“慨然入道”,企图通过宗教活动“使四海教风为一家”,以有益他抱负的实现。陈垣先生曾指出王重阳宗教活动的目的在于“隐然以汴宋之亡,欲与完颜、奇渥温氏分河北之民而治也。” 正确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由陕西出关,东至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政和以来被赵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弄的丧失人心的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创立了全真教。其教“屏去妄幻”,“以澄心定义,抱全守一”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为全真,而且,他还融合三教,以道教《道德清净经》、儒教《孝经》、佛教《般若心经》为教义,旨在用这三方面的思想将其拥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都笼络到手。王重阳以“会”作为全真教的基层单位,他曾于文登(在今山东东部)建立“三教七室会”,于宁海建立“三教金莲会”,于福山(今属山东)建立“三教三光会”,于登州(今属山东蓬莱)建立“三教玉华会”,于莱州(今属山东)建立“三教平等会”,“其会虽五,其约束规矩则一也,”性质恐怕已超出一般的宗教组织了。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过程中结纳了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中马钰(号丹阳)、丘处机(号长春子)、谭处端(号长真子)、王处一(号玉阳)、郝大通(号太古)、刘处玄(号长生子)、和马钰妻孙不二为骨干人物,是王重阳的法传弟子,俗称“七真”;王重阳死后,他们在北方广泛传播全真教。因为全真教和广大北方人民在感情上有一定的共鸣之处,所以在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势力发展很快,“南际淮,北至溯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由于它“惑众乱民”,所以,“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金章宗时下诏禁罢了全真教,全真教受到压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真教兴盛之初所具有的民族意识。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全真教骨干人物的地主阶级本质的逐渐显露,全真教也和其它宗教一样,最终蜕变成了统治者用来毒害人民的麻醉剂。如前所述,在成吉思汗的拉拢下,丘处机等人把这一宗教叛卖给元朝统治者,使它脱离了原有的反抗异族的精神,而成为异族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全真教也因此而具有了正统的宗教地位,转入了它的末流贵盛时期。
永乐宫的创建历史及其华贵的建筑格局和道宫经济状况,说明了它是元代全真教贵盛的产物,是元朝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一颗宗教苦果。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永乐宫创建之时,“百公劝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文事”,“陶甓伐木云集川流”,如此盛况,说明永乐宫的兴建是得到广大北方人民群众支持的,也表明了全真教并没有因为其领导人物政治立场的转变而脱离群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历史现象。固然,宗教的感情和传统影响也有一定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当时社会历史状况所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时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残酷,尤其是北方广大的汉族人民在社会地位上被列为第三等级,备受欺辱。蒙古人、色目人大多数又居住于大都附近和华北广大地区,他们在北方圈占掠夺土地,有的“或占民田近千顷”;有的“竟冒夺民田四十余万顷”;把称作“驱口”的农业生产者,当作私有财产,同牲口一样任意买卖。加之,元朝统治者频繁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骄奢淫逸,赋役繁多,使人民“多致破业失业”,沉重的劳役往往使劳动者“肩背成疮”,仍不放去。所以,当时北方广大汉族人民,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压榨,千百成群地逃往南方,仅在1238年中,南迁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之多。当然,在元朝统治的严密控制下,能够南迁的北方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仍旧留在北方处于火热水深的煎熬之中。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们投向了宗教的怀抱。在元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宗教,借以麻醉人民,泯灭人民的反抗斗志,所以给宗教以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宫观寺院享有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差役的权利。因此,北方广大群众把宗教当作逃避灾难的圣地乐园,纷纷加入宗教或者寻求宗教的庇护以减轻所受的剥削,求得继续生存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也里可温等一些宗教都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全真教由于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些特权,固然使全真教的上层人物迅速发展成聚敛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寺院地主,但也使信仰全真教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受到一定的保护,获得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北方广大群众对全真教的感情,既是他们对传统宗教的怀念,也是他们利用宗教来维护切身利益的一种反映。
当然,元朝统治者提倡全真教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其教“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已利人为之宗”的特点,软化北方人民的强烈反抗斗志。因此,在元代北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真教的末流贵盛,归根结蒂,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
金元之际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徒众多,宫观遍布北方。从整体上说,全真教的道观经济主要是教徒自己创造的。但全真教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道观经济来源,无论宫观、土地、财物和劳动力,都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的施舍和援助。这些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支援,对全真教道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金元之际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徒陡增,宫观相望,教团的规模空前扩大。因全真教实行出家制度,道观对教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时期的全真教徒,修宫建观,耕田凿井,自食其力;他们修道的同时又从事劳动生产,实际上是道观经济的主要创造者。但全真教的道观经济与世俗社会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经济来源而言,无论是宫观、土地还是财物和劳动力,都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的施舍和援助。
道观经济,一般主要由宫观及其所属土地构成,这两者是教徒居食的根本,而宫观的作用尤为重要。金末乱前,由于金朝禁止民间私创寺观,全真教只有少数道观,教徒主要以乞食为生。蒙古侵入中原后不久,全真教即受崇于蒙古贵族,成为当时北方官民争相敬奉的对象,全真宫观也蔚然而兴,遍布北方。其中有些宫观,就是当地官员给予全真教的。这主要有两种,一是战乱中被遗弃的旧有宗教场所,二是官员个人创建的道观。这些来源于官方的宫观,是全真教道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末战乱使很多宗教建筑被毁弃,当地官吏有时就把它们施给了全真教。全真教徒以此为基础,旧者新之,缺者补之,小者大之,务使其完整宏阔。如开州的神清观,本是灵显真君庙。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逍遥子张志仙云游至此,县令赵侯见而敦请留居该庙,“时往饷之”。志仙授徒数百人,声名远播。“会首蔡公喜其为人,以己庙侧之田文而畀之,别为卜筑缔构,俾居而庐之。安抚使王公嘉其制行严谨,裁成费助,浸兴是观。”后该观额日神清。山西芮城有纯阳祠,太宗十二年(1240)披云真人宋德方至此,拟改祠为宫,元帅张忠等人“将祠堂并地基尽具状以献,都统张兴又施水地三十亩,众人又施磨窠一区”;后冲和真人潘德冲以祠堂为基础大为营建,卒成拥有庞大产业的纯阳万寿宫。燕京玉清观是由五岳行祠发展而来的,主其事者是精通医术的马志希。志希于金亡后出家学全真,行医至昌州,结识一位“那演相公”。后来该相公以燕京府邸附近的东岳行祠为献,“又斥地得数亩”,创为玉清观。这种由官吏把当地原有宗教场所转给全真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这里仅举数端,以例其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教官观相对集中的区域,当地官员有时把宫观成批地转到全真名下。如泰山,“盖前古帝王封禅之所,其宫卫,其辇辂,其祠宇,自经劫火之后,百不一存”。东平行台严实素重事神,欲请“道价腾满齐鲁间”的天倪子张志伟予以修葺,志伟以工程浩大请辞,“武惠(严实)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资,与夫彩绘丹雘之费,我尽领之,师无让为,遂诺之”。经过三十多年的营葺,上至玉女祠,下至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外则岱岳观、朝元观,皆粲然一新,“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又如终南山,向为道教圣地,号称“天下洞天之冠”,但经兵火蹂躏,宫观多废。太宗五年(1233),田雄镇抚陕西,“治政之暇,兼崇道德,凡所营葺,皆力赞之”,由是秦地宫观多属全真教。田雄治秦伊始,即以灵虚观为基础扩建全真祖庭,“罄家赀以备奉葬之礼,以给营建之用”,“乙巳(1245),朝命增封为重阳万寿宫”。太宗七年(1235),田雄疏请掌教尹志平入秦,次年“将太平宫、楼观太一宫、佑德观、华清观、云台观,尽归于师”。同时又请刘志源修复上清太平宫,凡经营20年,雄深瑰丽。该宫的产业非常庞大,“赡宫下院,其观有四,京兆之长春、郝之清和、高陵之太一、郭南之灵仙,又金水、万里二水,皆道众日夕游息之地,故沿流上下,有台阁园圃焉”。这种规模的形成,实有赖于田雄及当地官府的庇护,“总管田侯洎众官属,自发疏以来,护其强梗,卫其侵侮,俾其阙乏,导其壅滞”,简直是该宫的守护神。其实这也是其他宫观之所兴复的重要缘由。
由官员个人创建的全真道观,数量也不少。这些官员基本都是全真教的忠实信徒。山西崞山有观日朝元,由崞山军节度阎德刚、阎镇父子所建。阎德刚治政之余,“颇与方外士周旋”,尤与全真道士梁思问友善,并“为之辟旁近西园,规作庐舍,以为谈经讲道之所”。阎德刚死后,其子阎镇继之,“庀徒蒇事,土木皆作”,修道所需,一应俱全。忻州太守张安宁是个狂热的全真信徒,他先把“所居之宅”改为观宇,供“道侣修香火而安居处”,继而又将定襄南邢村“先人之旧庐”舍为道观,“以修乡里之善缘”。且所需用度,“不烦隧正,不扰里胥,伐木集材,轮奂缔构,侯(即张安宁)悉出家赀为酬”。而河北新城县龙翔观则为元帅姬公所创。姬公名立斤,曾为宣德行军都元帅,因从征河南有功,分邑新城。“家又世袭打捕鹰房都总管,素宠道教,师事清虚至德草冠张真人,因以是观归之。”同时“又资南郭之田四百亩为赡恒产”。像这类由官员自建的道观,因属草创,规模当然无法与原有宫观相比,但其意义却非比寻常,它表明全真教对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信众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有些极端者甚至罄其所有也在所不惜。
全真宫观所属的土地,当以教徒耕占的荒弃地为主,但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官吏和民众的施舍。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成吉思汗两次传旨,指示燕京官员允许丘处机随地居住传教,“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爱愿处即住”,这为各级官员向全真教施以土地大开方便之门。如在燕京,为安置丘处机,“行省及宣差札八相公北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为献,且请为道院。师辞不受,请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为颁文榜以禁樵采者,遂安置道侣,日益修葺”。当然,这是丘处机以教主之尊所得的特殊待遇,其他道观动辄得地“数十顷”的情况则并不常见。
如前所述,全真教在关中地区颇受田雄的重视,原有宫观多归属全真。而在授予全真道观以土地这点上,田雄同样也非常积极。据姬志真《终南山栖云观碑》载:王志谨有任姓弟子者,元太祖二十年(1225)自燕至秦,欲以终南山重阳万寿宫附近一废庵为修道之所,后“承京兆府总管给据,令射占开擗住持”。任公率门弟苦心经营,“前后约七十余亩”,建为栖云观。王志谨另一弟子儒志久,太宗五年(1233)应田雄之请住京兆迎祥观,“暨而寻及夏侯之里,踌躇四顾,清绝可观,曩为名公达士游息采真之地,忍视芜没,纵狐兔豺狼之嗥啸于其间,遂择隐约,摭瓦薙荒垣而限之,经内外之田以亩计者二百八十有奇,立文以畀之” 。这些“射占”的土地,成为教徒日后衣食的重要来源。
同样,在全真教盛行的山东,地方官员向全真施以土地的例子亦不鲜见。如淄齐之间的般水镇旧有太清观,“金迁之后,戎马不息,相承者窜匿”,“权知济南府事范智、摄历城县事马通、主薄张彬,请临渊崇源大师刘志蕴住持,仍给田三十亩,粟百斛,以聚其徒,乃始剪榛莽,逐蛇豕,扶倾覆漏,增无补缺”。此外,须特别注意的是莱州神山洞。该洞由披云真人宋德方所凿,所得土地是当地官员根据蒙古统治者的旨令而给付的。据《神山洞给付碑》:乃马真后称制四年(1245),宣差莱登州长官都帅得旨:“伏见莱州神山洞乃古迹观舍,屡经兵革,未曾整葺。今者幸有披云真人糺领迢众,虔心开凿仙洞,创修三清五真圣像,中间所费功力甚大。其山前侧佐一带山栏荒地,除有主外,应据无主者尽行给付本观披云真人为主,裨助缘事,诸人不得诈认冒占。”这种由蒙古最高统治者命地方官直接划给全真教土地的记载虽仅此一见,但足以显示全真教在经济来源上所具有的深刻的政治背景。
当然,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官员向全真道观施舍土地。山西晋城的会真观本系民宅,初由全真师杜志元改立为庵,但规制简陋,海迷失后称制元年(1249),“泽州次官赵公唐以杜氏之地屋并司氏所施地亩,俱给赡庵,约百亩余。……其土沃衍,乃福地也”。济源太清观经丧乱兵烬,荡为瓦砾,济帅杨公闻王处一弟子单志静栖心于此,“重师之道德,请留住是观,施其周围良田百有余亩,为功德主者”,后额为太清万寿宫,成为“济上琳宫玄苑传道焚修、祝延国祚之名所”。
与官方相似,民间把土地舍人道观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山东益都白云观始建于金末。其时全真弟子韩抱真避兵流落至此,“有会首马公,素重先生之道德,因以其地施焉”。抱真与其徒“结茅其上”,日营月葺。后又有会首施田,前后总计“田六十亩,尽充观之常住,赡养徒众焉”。山西芮城的玉京观也创于兵劫之余,起初只是仅蔽风雨的小道庵,据说因庵主薛志熙“凡所祈禳,无不应感”,“是以一方士庶,倾倒信奉,割地输财,助工借力,共成胜事”。“又有所谓广田亩,拓道路,植艽椒,栽桃李,左右前后园圃一新”,终“变荒田为福田”。同在芮城的乐全观,“始于圣朝之丁酉(1237),有西黑李福成割己业一十亩以施于河府郭。越七年癸卯(1243年),又弃中间地七亩,以施于灵峰杨,及枣林平,以资日用之费,而郭、杨二公各主持之”。后该观主于披云真人宋德方。另外,在河南怀吉,原金将宋道安人全真后相继创有丹阳和林泉二观,前者是当地官员赠以卫氏豪族废宅而建立,而后者即是基于医者梁辑所施家业而建立。梁辑“医穷难素,道慕邱刘,将城东村所居别墅屋宇,地土桑枣,罄而施之于公。公于是又立林泉观”。这些由民间捐出的土地,在全真教道观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除宫观和土地之外,全真教得自社会的援助还有财物和劳动力。相对来说,财物来自官方施舍的力度较大,而民间的较小。但在劳动力的援助上,则主要出自普通百姓,这种无形的人力支援,对全真教的道观经济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全真教修宫建观,必然需要大量经费,而官员的资助无疑是其重要的来源。在这方面,蒙古宫廷有时也会伸出援手。奥敦妙善本系女真贵族,金泰和四年(1204)出家学全真,元宪宗五年(1255)主亳州洞霄宫,并承怙哥火鲁赤作护持功德主,大起营建,“以祀全真祖师”。奥敦妙善“与其徒任惠德辈,以淳诚德誉贵近,获入觐禁闱,中宫及诸贤妃皆尝赐召,赐予极优渥,所得金帛,悉以充洞霄桩严之具,故得受业者,恒及千指,内外无间言”。也就是说,这些得自中宫的金帛,均用以装饰殿宇、扩收门徒。蒙古后妃除亲赠财物外,有时也指示地方官帮助“修盖”。如太宗十二年(1240),东宫后妃就曾发布懿旨给平阳府路达鲁花赤管民官,要求在“雕造道藏经并修盖等事”上提供协助,其中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的“修盖”就得到了沁州长官杜德康的倾力资助。该宫初由主持编纂《玄都宝藏》的宋德方倡议翻修,可能由于资金问题久未覆瓦,后有任事者“忻然愿结此胜缘,然共计买锡资并酬诸工匠价,约用白金伍佰两”。工费如此浩大,又“遽遭岁旱”,以致费用仍无法筹措到位,于是该宫提点李志昭决定去沁州长官杜德康处化缘。杜德康与其夫人王体善素崇全真,李志昭“具说天坛上方结瓦硫璃宝殿阙费之事,艰剧之由。长官、夫人一闻言而俱便首肯,乃曰:‘某等昔年钦奉朝旨,令提领雕造三洞藏经,兼修建诸宫观事,素有增饰上方念。今提点又言,正符前意。弊家虽财力浅薄,愿落成之,费用然多,更无他适,直圆备三清大殿了耳。”’杜德康因此被三洞讲师李志全赞为“宽大长者”。
前已叙及的京兆总管田雄,除施观施地外,还尽其所能给以经费支持。因为且不说新建道观,即使是施与全真的原有宫观,也多毁于兵火;何况“秦为兵冲,焚毁尤甚”,予以修复必然需要巨额费用。从商挺《增修华清宫记》判断,田雄等官员为此当给以很大的经费支持。长安华清宫自唐以来素为道教名观,商挺在金末乱前看到该宫尚“重楼延阁,层台邃沼,虽不迨承平盛时,而规模制度,宛然故在”,但兵后却沦为榛莽之区。不过宪宗三年(1253)他“复过故宫”,“荡然无复向日”,“丹垩藻绘,粲然一新,若初未毁,而又有加焉者”。问其故,则知除四方道侣“成愿荐力”外,“又得太傅移刺公、总管田公,输赀助役,相与翼成”。这虽是华清宫的情况,但考虑到田雄帮助全真的热忱,想必其他宫观有的也会得到他的“输赀助役”。同样,金末蒙初山东红袄军领袖、降蒙后被授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的李全及其夫人杨妙真对全真教也给予很大的经济援助。太宗三年(1231),李全攻宋败死后,杨妙真袭职行省达数年之久。此前,大约从丘处机应召西行时起,栖霞太虚观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其经费就有相当部分来自杨妙真的赞助,是谓“及蒙行省李公夫人杨氏为外护功德主,凡所不给,悉裨助之”。可以说,杨妙真、田雄与前已叙及的东平行台严实等地方实权人物,对全真教道观经济的发展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一般官吏向全真教提供的财物支持则更具普遍意义。马钰故里宁海有玄都观,额于金泰和六年(1206),贞祐之乱被毁,蒙古人据河北地区后得以重修。其营修费用,实赖宁海州刺史姜思聪和管民长官姜思明兄弟的鼎力支持。姜氏兄弟“政成多暇,邃览重玄,喜捐珍物,茂赞仙风。以次名宦显仕,大贾富商,各输帑藏之丰,统助盛缘之广费。经营靡辍,缔造落成”。后该观于元定宗三年(1248)改称玄都宫。巨野的妙真观本为茅庵,初由云溪散人田妙真所创。妙真“化行四方,所积得富”,乃“别议缔构”。“其前后辅赞经构之费,县令高君琛,巡检桑君德佑,前管民提控田君宽,前县令翟君皋,前军民弹压桑君德荣,前营民提控吴德、郭全、尹德数君,尤之为甚。”既成,“雄丽 靖深,甲于一方”。又如山西元都清虚观,其创始者高志辅开始“寄迹于此峻岩之下,穿穴而跧,乞余而食”,里人“见其状貌高古,举止清儋,知其不凡”,于是商议筑垣起舍以居之。“长官王伯昌、副贰官陈资寿闻其风而悦之,各捐贿,起三清之邃宇,建五祖之华堂”。堂宇如此壮丽,可见当地官员“捐贿”之多。当然,有时官吏弃职入全真后,以前结交的官员更愿意出资相助。如燕京丹阳观,“全真道师通玄子刘君所建也”。据说“通玄子才气迈爽,年二十余辟王府参谋,委任近密”。忽然悟世空华,遂“散财弃妻子”,“修全真教”,道众欲推为燕京长春宫提点,亦“非所乐也”,“故所交游达官贵人,竞施财物,助之买地致材,以建此观”。
对多数信奉全真教的普通民众而言,独力建观非力所能及,施舍田地又影响自身生活,但本地建观又不能无动于衷,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些财物特别是劳动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据《栖真子李尊师墓碑》:太原天庆宫毁于兵乱,李志明志欲兴复,“即荷畚锸为之倡,从之者云集,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师斡旋运动于神明之中,而应之者不愆于素,遂使天庆之规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者”。这种“从者云集”的营建景象,又见于秦志安《重修玉阳道院记》:玉阳道院在古洛西南,干戈稍息,遗民稍集,即有全真徒段志寥、姚志玄来修葺经营。“东郊西社,南邻北里,见先生之慎言语,谨行止,皆擎拳曲跽而为之礼,比比若慕膻之蚁,皆曰:……先生之来撑拄玄关,扶持教垒,安可以袖手旁观而掩襟坐视乎?于是富者为之舍财,巧者为之献技,拙者为之竭劳,辨者为之赞成而已。”又据《创建岱岳行宫记》:河阳县西里仁村民劫后得以余生,以为有神灵护佑,决定建行宫以崇祀岱宗之神。“自是一方之人,富者输材,贫者施力。斧斤者敬效其能,绘画者愿施其巧,陶甓者不召而从,污漫者不戒而至。”该观创始于太宗十三年(1241),由全真教徒住持致祭。另,渑池县义丰乡西张村有古禹庙,全真弟子李元常以为“仙侣胜地”,“遂与乡人岁时致祭,屋宇虽曾更新,终为旧贯,树志潜谋,于庙东始剪荆棘,创立观院,垦田兴农,以为永远之基”。新观名曰“兴国”,“凡所兴修,多资众力”
与普通民众相似,对兴观崇教这样的功德,民间豪右当然也乐于参与。辉州有地名日“请佃户”,其民李宝者慕全真之学,施地以为建观之基,但陈志玄营葺而未见其成。于是其徒鲁志瑞“遍谒里中之豪,得其资力,庀徒蒇工,旧者新之,小者大之,无者起之,不足者补之,不期年而工毕”。殿宇完备,又“赢市地于四邻,合旧为六十余亩”,可见乡里豪右“资力”之厚。嵩山有崇福宫,原其所自,在汉为万岁观,在唐为太乙观,在宋为太乙宫,早已名闻天下,但金季毁于兵火。全真徒乔志高以道术名于时,“其禳祷,其感通,应诸如神,百祈百验,豪士贵公,奉从颇口”,因此他在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2)开始兴复该宫时,“远近豪右知之,或割地,或输财,填辏其门”。志高住持崇福宫近三十年,至中统五年(1264)他登真(去世)时,该宫“产业赀基,足能赡众”。这里的“产业”,应有相当部分来自豪右的施予。类似的事例还很多,兹不备举。仅从上述两例来看,有些全真道观“产业”的形成,与民间豪右的资助也有很大关系。
须说明的是,全真教道观经济的社会来源,表面看来自官民两途,但实际上某些宫观的经济乃得益于官民的共同施舍,其间并没有严格的官民界限。如据《大元国广宁府路尖山单家寨创建大玄真宫祖碑》:杨志谷在广宁府单家寨谋立道观,“蒙北京路都元帅兀也儿,及本府主官失剌万户,为外护功德主,暨一方官僚士民,或施之以财,或助之以力,所以赞成胜事也。清和大宗师题其额日玄真”。又《顺德府通真观碑》:李志柔等人在顺德府城西南隅建观,“又得郡守安国军节度使赵侯伯元为功德主,于是远近响应,缘力日振。”“其为屋凡四十间,为像凡二十一躯,为地合六十亩。”“观之南别置蔬圃,以资道众。”可以说,该观的产业,是依靠官民共做“功德”而形成的。与此相似,泰安的会仙观自太宗四年(1232)开建,后泰安刺史张侯为之倡导,“百役具举,凡所缺乏者,侯皆裨助之。由是乡邻远迩莫不响应,富者以财,贫者以力,日构月缔”。正因“外护有郡侯,多助有居民”,所以仅十余年,殿堂厨库,蔬圃井硙,无一不备。约与泰安会仙观起建的同时,在陕西蒲城,“节使吴帅、经历刘君”也举地建崇真观,“若夫富者以财,贫者以力,初不召而自臻”。观之产业,“公则有据,私则有券”,殊无冒夺之患。这些情况均说明,金元之际全真教有些道观的经济,无论王侯商贩,都共同给予了一定资助。 综上,金元之际全真教的道观经济,无论是宫观、土地,还是财物和劳动力,都得到了世俗社会的大力支援。《大元重修聚仙观碑》引称道教宫观之兴有三种“缘”:“真仙出世处为自然缘”,“国家崇建为遇时缘”,“道者勤诚感众为功行缘”。而金元之际的全真教即兼有“遇时缘”和“功行缘”两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的宠遇和社会信众的施舍,全真教无一不备,正因为如此,全真教的“华宫壮观”才得以“星罗夷夏”,庞大的教团在经济方面才有了重要保障。